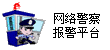从2019年的暴利猪周期到2022年后的微利猪周期,业内人士都爱谈规模养殖集中化。
除开众所周知的大型上市猪企市场占有率提高之外,另外一部分在农村的“腰部群体”也在壮大。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前往云南曲靖、广西南宁等多地调研发现,规模化养殖户更倾向于育肥代养模式,有从“农户加公司”到“公司加公司”的趋势呈现。
在“公司加公司”的模式中,农户养殖户通常作为投资者,聘请过去在农村有经验的养猪人养猪。尽管育肥代养模式具有结算价格的稳定性,但要想进入市场也不容易,首先要过猪场选地关。
育肥的稳定价格成为吸引点
养猪之前,来自曲靖市陆良县的何伟是养殖白羽肉鸡的。白羽肉鸡是大众熟知的品种,它的供货主力就是肯德基、麦当劳等。然而白羽肉鸡的出栏周期短,周期波动大。后来,何伟压根就不养鸡了,2018年后转行养猪。
34岁的龚化江在大学学的是兽医,毕业之后没有干本行,转头去卖饲料。卖了一段时间饲料又转行,从2018年后开始养猪,搞起了自繁自养——从母猪端到育肥为一体的养殖模式。
对于养猪人来讲,2018年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养猪人都看标准的猪周期——以四年为一个单位,猪价高点多养猪,猪价低点少养猪。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因为非洲猪瘟的出现,猪周期的内在平衡被打破,前所未有的超级猪周期来临。
养猪的暴利年份在2019年到来,巅峰时期养一头猪能挣3000元。
然而何伟和龚化江不敢挣这个“暴利”,转而为云南的大型猪企神农集团(605296.SH,股价29.05元,市值152.47亿元)代养育肥,挣一个稳定价格。
同样做出这一选择的还有他们隔壁县的李红斌。李红斌有一个亲戚,他是嗅觉灵敏的生意人,在四川经营了一家大型的摄影公司。在2019年,李红斌的亲戚就鼓动他养猪:“猪价一定会涨,要挣大钱。”然而时至今日,李红斌都没有选择从猪价波动中挣大钱。他做出同何伟、龚化江一样的选择——和公司合作,为其育肥。
这种模式就是熟悉的“农户加公司”,公司与农户签订合作放养育肥合同,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形成一个基础单价,该基础单价会在回收结算时根据市场最新变化适当浮动。当育肥猪达到可出栏的体重时,对其进行称重,由基础单价乘以均重形成基础价格,再根据具体猪只的重量是否超出或不达理想体重区间、上市率(即成活率)、正品率、喂养天数、总增重、全程料肉比、日均增重、超标耗用饲料等生产指标,对结算价格进行调整,得到最终的代养费。
上述养殖户与神农集团的育肥结算价在每公斤16.8元左右,每头猪的结算收入大概在200元到300元上下浮动。
与上述养殖户不同的是,只有高中学历的武竹平已经是老养猪人,然而她的选择仍然是代养。武竹平告诉记者,自养转变为代养主要还是为减轻投资压力和市场风险。自繁自养的模式是重资产投入,产业链的风险由养殖户承担。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
曾经的散养户“回流”“腰部群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生物安全防控的压力是上述养殖户不约而同选择代养的重要原因之一。
非洲猪瘟的威胁之下,养殖户结构发生变化,也就是俗称的“去散户化”。据一财,全国畜牧总站一位首席专家曾在今年8月下旬的一次生猪产业论坛上表示,自非洲猪瘟暴发后的5年内,规模以下的生猪散养户,已经减少1300多万户,同比减少41%。
据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居前十的上市公司合计出栏约1.5亿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份额约为20.53%,较2022年有所提升。截至2022年末,一家头部养猪企业在养肥猪投放存栏的合作放养农户为2211户,较2021年末增长19%。养殖户平均规模较2021年末提高了40%。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去散户化的规模化进程中,一方面是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提升,另一方面武竹平这类“腰部”的规模化养殖户市场集中度在增长。
在神农集团的媒体采访会上,神农集团养殖事业部云南战区二总经理闪保剑表示,与神农集团合作的养殖户数量已经从2023年的373户提升至2024年9月的530户。公司副总裁、养殖事业部总经理顿灿表示,“越来越多人加入集团化养猪,‘单打独斗’的散养户在减少”。
根据闪保剑和神农集团养殖事业部广西战区总经理胡广胜的介绍,神农集团最小养殖户规模在500头左右,目前,广西地区最大单体规模达到3万多头。
何伟、龚化江以及武竹平三位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均在4000头以上,何伟的养殖规模更是高达2万头。
实际上,养殖散户的界定并没有明确标准,通常以500头养殖规模为分界线。
那么,消失的散养户去哪里了?
记者了解到,这一批散养户并非离开了市场,而是以场长等身份回到了市场——完成分工结构的“迂回生产”。最典型的就是李红斌,他告诉记者:“养猪只是我投资的一部分,我找了会养猪的帮我管。”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李红斌并不熟悉自己养猪场具体的料肉比等关键数据,他最开始说了一个“2.7”的数,说出后马上被纠正为“2.4左右”。他不会每天来猪场探查,对其了解更多的是生物安全方面,生产管理交给了神农集团师宗服务部经理赏文鹏,并请了一个从其他猪场离职的场长朋友来打理。
胡广胜提到一个新的养殖户分工变化——在个别区域出现“农户+公司”模式转为“公司+公司”模式,“代养越来越专业,老板作为投资人,请专业团队开展代养业务”。
就在11月5日,牧原股份首席财务官高曈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谈到养殖行业多元化分工形式的转变,他把这一过程形容为“有意思的转变”。
“过去我们会认为在行业里面有一批人做自繁自养,有一批人专门养母猪,有一批人专门养肥猪,会有这样的分工。但现在这种分工被更多元化的打破了,现在已经完全无法去量化或者定义从业者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段。”他说,有养殖户会买怀孕猪,孕猪产子之后可能会把仔猪销售掉,也可能自己养。有些养殖户会租猪场,或者用自己猪场去买仔猪,买15公斤的保育猪,买更大的30公斤到50公斤的肥猪,也有可能买110公斤的肥猪。现在,从业者从业形式非常多样化,是行业在过去波动下出现的一种趋势。
猪场选址是重中之重
实际上,无论是“农户+公司”还是“公司+公司”,其本身是规模化育肥的投入风险比控制在最小。
记者在南宁、红河州的实地探访发现,养殖户更倾向于租赁或改造闲置过的猪舍。即便如此,猪舍改造过程仍然是不菲的投资,上述养殖户投资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
这也就意味着在收入和投入比上,规模化养猪对养殖户而言仍然是重资本投入。具有一定资本的养殖户做固定资产投入,然后再聘请农村的养猪人当场长。个人出于降低风险以及稳定猪苗供应的考虑,大型公司就构成了市场分工的另一环。
为了将生物安全控制做到极致,养殖户仍然需要持续投入固定资产。
“我今年投了50万(元),专门去改造自动化料槽。”武竹平指着今年搭建的自动化取料设备。这是一根连接着外面料塔的不锈钢管,通过自动投料减少与人接触。
自动化饲料输送料管图片来源:每经记者胥帅摄
闪保剑表示:“越来越多人选择租赁,大家都在追求投资回报率,自建是一种重资产模式。”
因为有公司“兜底”结算费用,加上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标准化,养殖户也愿意在微利的猪周期扩产。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两点,其一是猪场选址,场地选址好坏对生物安全防控有“致命”影响。
李红斌的猪场就选址在农地里的上风区域,龚化江则把猪场选在养猪区域里“制高点”。49岁的韦振文,一直在崇左市扶绥县养猪,他的猪场选址地点更是“当道下寨”——猪场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通行。
其二是猪苗的良种率,这将影响后续料肉比、PSY(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死淘成本等关键指标。51岁的韦培东在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养猪,他换了公司合作育肥。更换公司合作的主要原因是猪苗稳定率。
胡广胜表示,代养市场的竞争也较为激烈,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市场。在顿灿看来,这一种“双向选择”是生猪养殖的剧烈变化,“都在追求增效降本,包括种猪基因、生产水平、智能化、数字化等,只有提升全产业链的经营能力,才能在这个新的时期实现更好发展”。
除开众所周知的大型上市猪企市场占有率提高之外,另外一部分在农村的“腰部群体”也在壮大。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前往云南曲靖、广西南宁等多地调研发现,规模化养殖户更倾向于育肥代养模式,有从“农户加公司”到“公司加公司”的趋势呈现。
在“公司加公司”的模式中,农户养殖户通常作为投资者,聘请过去在农村有经验的养猪人养猪。尽管育肥代养模式具有结算价格的稳定性,但要想进入市场也不容易,首先要过猪场选地关。
育肥的稳定价格成为吸引点
养猪之前,来自曲靖市陆良县的何伟是养殖白羽肉鸡的。白羽肉鸡是大众熟知的品种,它的供货主力就是肯德基、麦当劳等。然而白羽肉鸡的出栏周期短,周期波动大。后来,何伟压根就不养鸡了,2018年后转行养猪。
34岁的龚化江在大学学的是兽医,毕业之后没有干本行,转头去卖饲料。卖了一段时间饲料又转行,从2018年后开始养猪,搞起了自繁自养——从母猪端到育肥为一体的养殖模式。
对于养猪人来讲,2018年是一个节点。在此之前,养猪人都看标准的猪周期——以四年为一个单位,猪价高点多养猪,猪价低点少养猪。然而也就是这一年,因为非洲猪瘟的出现,猪周期的内在平衡被打破,前所未有的超级猪周期来临。
养猪的暴利年份在2019年到来,巅峰时期养一头猪能挣3000元。
然而何伟和龚化江不敢挣这个“暴利”,转而为云南的大型猪企神农集团(605296.SH,股价29.05元,市值152.47亿元)代养育肥,挣一个稳定价格。
同样做出这一选择的还有他们隔壁县的李红斌。李红斌有一个亲戚,他是嗅觉灵敏的生意人,在四川经营了一家大型的摄影公司。在2019年,李红斌的亲戚就鼓动他养猪:“猪价一定会涨,要挣大钱。”然而时至今日,李红斌都没有选择从猪价波动中挣大钱。他做出同何伟、龚化江一样的选择——和公司合作,为其育肥。
这种模式就是熟悉的“农户加公司”,公司与农户签订合作放养育肥合同,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形成一个基础单价,该基础单价会在回收结算时根据市场最新变化适当浮动。当育肥猪达到可出栏的体重时,对其进行称重,由基础单价乘以均重形成基础价格,再根据具体猪只的重量是否超出或不达理想体重区间、上市率(即成活率)、正品率、喂养天数、总增重、全程料肉比、日均增重、超标耗用饲料等生产指标,对结算价格进行调整,得到最终的代养费。
上述养殖户与神农集团的育肥结算价在每公斤16.8元左右,每头猪的结算收入大概在200元到300元上下浮动。
与上述养殖户不同的是,只有高中学历的武竹平已经是老养猪人,然而她的选择仍然是代养。武竹平告诉记者,自养转变为代养主要还是为减轻投资压力和市场风险。自繁自养的模式是重资产投入,产业链的风险由养殖户承担。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
曾经的散养户“回流”“腰部群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生物安全防控的压力是上述养殖户不约而同选择代养的重要原因之一。
非洲猪瘟的威胁之下,养殖户结构发生变化,也就是俗称的“去散户化”。据一财,全国畜牧总站一位首席专家曾在今年8月下旬的一次生猪产业论坛上表示,自非洲猪瘟暴发后的5年内,规模以下的生猪散养户,已经减少1300多万户,同比减少41%。
据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居前十的上市公司合计出栏约1.5亿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份额约为20.53%,较2022年有所提升。截至2022年末,一家头部养猪企业在养肥猪投放存栏的合作放养农户为2211户,较2021年末增长19%。养殖户平均规模较2021年末提高了40%。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去散户化的规模化进程中,一方面是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提升,另一方面武竹平这类“腰部”的规模化养殖户市场集中度在增长。
在神农集团的媒体采访会上,神农集团养殖事业部云南战区二总经理闪保剑表示,与神农集团合作的养殖户数量已经从2023年的373户提升至2024年9月的530户。公司副总裁、养殖事业部总经理顿灿表示,“越来越多人加入集团化养猪,‘单打独斗’的散养户在减少”。
根据闪保剑和神农集团养殖事业部广西战区总经理胡广胜的介绍,神农集团最小养殖户规模在500头左右,目前,广西地区最大单体规模达到3万多头。
何伟、龚化江以及武竹平三位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均在4000头以上,何伟的养殖规模更是高达2万头。
实际上,养殖散户的界定并没有明确标准,通常以500头养殖规模为分界线。
那么,消失的散养户去哪里了?
记者了解到,这一批散养户并非离开了市场,而是以场长等身份回到了市场——完成分工结构的“迂回生产”。最典型的就是李红斌,他告诉记者:“养猪只是我投资的一部分,我找了会养猪的帮我管。”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李红斌并不熟悉自己养猪场具体的料肉比等关键数据,他最开始说了一个“2.7”的数,说出后马上被纠正为“2.4左右”。他不会每天来猪场探查,对其了解更多的是生物安全方面,生产管理交给了神农集团师宗服务部经理赏文鹏,并请了一个从其他猪场离职的场长朋友来打理。
胡广胜提到一个新的养殖户分工变化——在个别区域出现“农户+公司”模式转为“公司+公司”模式,“代养越来越专业,老板作为投资人,请专业团队开展代养业务”。
就在11月5日,牧原股份首席财务官高曈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谈到养殖行业多元化分工形式的转变,他把这一过程形容为“有意思的转变”。
“过去我们会认为在行业里面有一批人做自繁自养,有一批人专门养母猪,有一批人专门养肥猪,会有这样的分工。但现在这种分工被更多元化的打破了,现在已经完全无法去量化或者定义从业者究竟是属于哪一个段。”他说,有养殖户会买怀孕猪,孕猪产子之后可能会把仔猪销售掉,也可能自己养。有些养殖户会租猪场,或者用自己猪场去买仔猪,买15公斤的保育猪,买更大的30公斤到50公斤的肥猪,也有可能买110公斤的肥猪。现在,从业者从业形式非常多样化,是行业在过去波动下出现的一种趋势。
猪场选址是重中之重
实际上,无论是“农户+公司”还是“公司+公司”,其本身是规模化育肥的投入风险比控制在最小。
记者在南宁、红河州的实地探访发现,养殖户更倾向于租赁或改造闲置过的猪舍。即便如此,猪舍改造过程仍然是不菲的投资,上述养殖户投资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
这也就意味着在收入和投入比上,规模化养猪对养殖户而言仍然是重资本投入。具有一定资本的养殖户做固定资产投入,然后再聘请农村的养猪人当场长。个人出于降低风险以及稳定猪苗供应的考虑,大型公司就构成了市场分工的另一环。
为了将生物安全控制做到极致,养殖户仍然需要持续投入固定资产。
“我今年投了50万(元),专门去改造自动化料槽。”武竹平指着今年搭建的自动化取料设备。这是一根连接着外面料塔的不锈钢管,通过自动投料减少与人接触。
自动化饲料输送料管图片来源:每经记者胥帅摄
闪保剑表示:“越来越多人选择租赁,大家都在追求投资回报率,自建是一种重资产模式。”
因为有公司“兜底”结算费用,加上生物安全防控体系的标准化,养殖户也愿意在微利的猪周期扩产。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两点,其一是猪场选址,场地选址好坏对生物安全防控有“致命”影响。
李红斌的猪场就选址在农地里的上风区域,龚化江则把猪场选在养猪区域里“制高点”。49岁的韦振文,一直在崇左市扶绥县养猪,他的猪场选址地点更是“当道下寨”——猪场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通行。
其二是猪苗的良种率,这将影响后续料肉比、PSY(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死淘成本等关键指标。51岁的韦培东在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养猪,他换了公司合作育肥。更换公司合作的主要原因是猪苗稳定率。
胡广胜表示,代养市场的竞争也较为激烈,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市场。在顿灿看来,这一种“双向选择”是生猪养殖的剧烈变化,“都在追求增效降本,包括种猪基因、生产水平、智能化、数字化等,只有提升全产业链的经营能力,才能在这个新的时期实现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