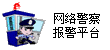相比陈雄伟 ,新丰镇金丰村刘天柱的养殖规模要大得多。“以前把一头猪养来 125公斤卖掉,这个过程中不收费,最多收取两三块钱的检疫费,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每年要多给汉塘公司交10万元左右。”
在刘天柱看来,汉塘公司名义上收取的是“三废”收集处理服务费,但实质是对每头猪进入市场收取的“人头费”。按照他的估算,从去年中成立以来,汉塘公司针对新丰镇的养殖户已经收取800多万元的服务费,而今年至少会有1600万元的进账。
不过,竹林村支书陈云华表示收费常态:“虽然目前养猪亏本,再加上环保压力,但在收取排污费时农户们大多没有抵触,都很了解这是为大家的环境做奉献。”
强制减产后果严重
为了控制规模,嘉兴正通过划定禁限养区、严控区外过路猪等政策调减生猪饲养总量,海宁、平湖等多地也推出了类似政策。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我们已经打算三年以内,请求关停部分养殖场。实行生猪减量体质发展,压缩总量,在县区精养区,3年内不翻建扩建猪舍,并关停部分养殖场,另给猪棚转产补助,引导农户转产转业。”
黄军分析,压缩后,新丰镇的存栏量将从现在的25万头压缩来 15万头,3年内,现有养猪的4.5亿的产值,将会缩减一个多亿。替代养猪的有几种途径,将农户现有猪棚改造成蜗牛棚,养殖白玉蜗牛。
“养了10来年猪,说养蜗牛就能养的吗?”陈云华说:“我们去年组织参观了白玉蜗牛的养殖户,养蜗牛技术含量很高的,但风险更大。如果蜗牛发生了疾病,很可能全部死光。”
“养猪的小散户,在我们农业规模化和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是第一 被剿灭的对象。”一些小散养殖户对此政策反应猛烈 。
据《中国经济周刊》费解,在嘉兴平湖塘等地,一些小散养殖户的猪舍已经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扩建猪棚被限制,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猪棚将被拆迁。有养殖户估量 称:“有多少猪棚有合法手续?如果把非法搭建的猪棚拆光的话,猪价来 几年后将翻两番。”
事实上,在养殖业发达的国家中,除了美国推行的大规模养殖外,在澳大利亚、日本都推行的是“散养户+合作社”的模式。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期指出:散养的小农经济模式才可以保证肉品质量,而大规模工业化养殖,因为片面追求市场利润,会导致品质下行。
有养殖户还指出,在养猪的产业链上,牵涉了玉米大豆的种植户、饲料加工厂、饲料分销店、猪肉食品厂,当然也有很多寄生在这条产业链上的中介,中间的从业人员非常多,光靠行政打压缩减饲养规模,后果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赵磊 | 浙江报道 文中涌现的养殖户,除宏正牧业负责人王波外,其余应受访者请求,均为化名)